12月12日下午,诗人、译者、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华体会体育
副教授李金佳老师莅临北外暮思厅,为线上线下总共约60名师生作了讲座,题为《昏昏与昭昭:如何翻译你自己读不懂的诗》。李老师从翻译的“不定意”问题谈起,引领听众品读了顾城诗歌和部分法译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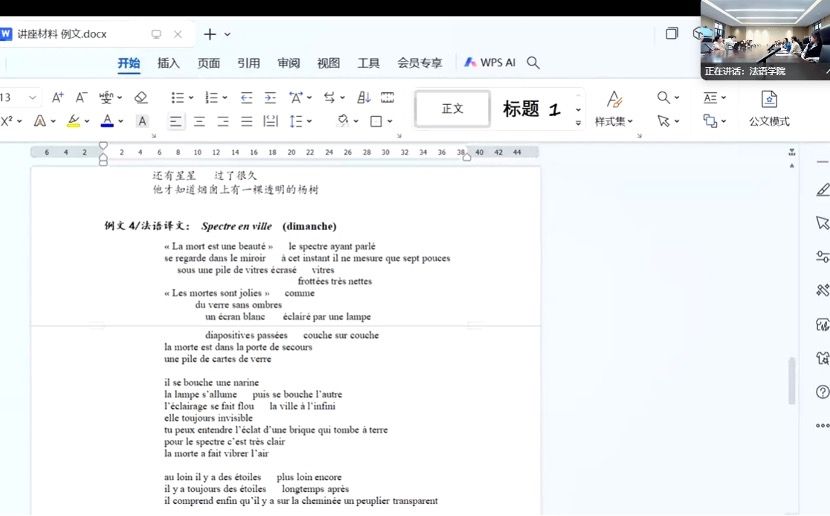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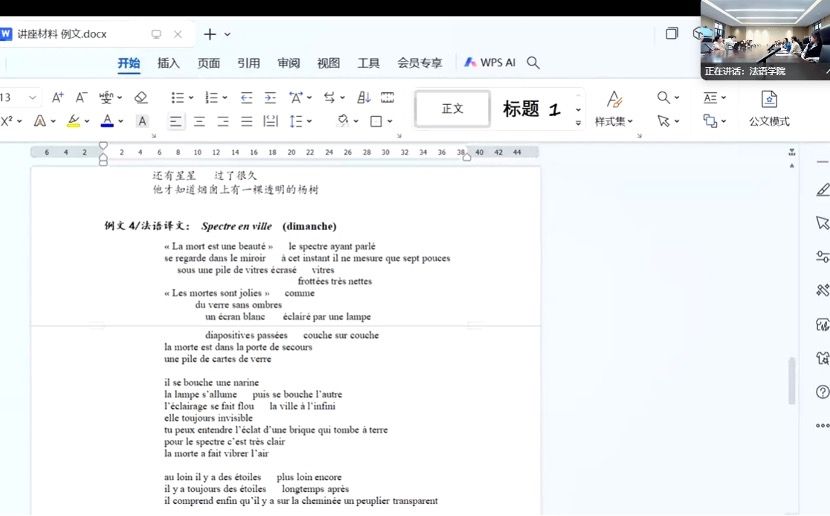
标题缘起于李老师的北外岁月。当年的翻译课流行一句对孟子原文的戏仿:“以己之昏昏而使人之昭昭,不亦难乎?”译前通晓原文对翻译固然重要,但在现代的试验性诗歌内部,文本的不可解性已根深蒂固,诗歌本身成为对意义的超脱,译者须以昏昏使读者昭昭。李老师选择的是顾城晚期组诗《激流岛话画本》、《布林的档案》和《鬼进城》的法译文,由 Yann Varc’h Thorel和刘耘合译而成。译文忠实而优美,或许淡化了原文的巧俏,却提升了思想的腾跃之感,为双语者理解顾城另辟了幽径。
《鬼进城》的《星期四》中,词句的意义悬置飘忽,不断朝多向生发,使诗在无限的多义中走向了反意义。70年代末,诗歌转向表现为对意义的抵牾与抗拒,明朗的意义、词与词先在的/权威主义的结合开始消弭。俄国形式主义中的陌生化也以破除意义为第一意义,顾城诗亦如是——无意义以有意义的方式展开,诗人对意义的叛逆导向了死亡的虚无与解脱,引向诗歌必然穿过而无踪影的雪地。
李老师指出,翻译与阅读不尽相同,不理解并不妨碍阅读。我们通过记忆让诗如病菌一般在体内潜伏,等待它随痛苦或缺失的经验二次出现,而翻译却是要传达原文的不可甚解。诚实地、规则地、紧贴原文地“昏昏”,则能为读者画下“昭昭”的入山符。例如,《布林》中的《发现》的译文意义向着略微明确、丰满的方向偏离,昏昏并未妨碍翻译。而对《布林》中的《谁能想到》中的“铜簧”,译者需要斟酌与上下文音响世界相契合的译法。《鬼进城》的《星期日》中,译文选词的阴阳性则是一种让诗中主客体对立明朗化的决断。
诗使人反思让文本成为问题、让诗不可甚解的因素。汉字单字化和赤裸化让汉语由表意的符号退化至史前的河姆渡时期,与上下文孤绝,成为字谜式的使用;歧义不是缺陷,而是诗歌的手段,多种读法的共存彰显着汉语的柔韧;谐音问题让看和听引发意义的混淆,使诗向无意义倾坠。意义往往在过渡之中变幻,在有无之间滑移。在顾城诗里,大量意象的叠加产生了意义的麻团,过分表意反而导向了无意义。该组法译本为解决或不解决上述情况的翻译提供了思路,译者眼光的烛照使译文更清晰,使翻译有了意义。
讲座末尾,李金佳老师借问答环节继续了对翻译的探讨。李老师以诗人的目光穿透行句本身,为听众带来了灵动开放的阐释,展示了翻译所呼唤的严谨与谦卑,是诗歌翻译的方法论,也是诗歌阐释的生动导言。
(撰稿人:程弋)